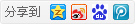文化的根在哪儿?不在殷墟,也不在故宫,在民间,在草根里。古人云:礼失求诸野。这话蕴涵深厚,耐人寻味。最基本的道德观念、是非观念,都是在民间坚持下来的,它像一条不息流淌的潜流。历朝历代的首脑,都搞愚民,但百姓有了抗药性,反倒更聪明了,最后总是皇帝败下来。百姓收拾罢残局,又开始应付新来的。一些倒了霉的人物熬过劫难,是谁掩护、救助的?正是那些“无知无识”的乡间野老。我还多次听到百姓机智地保护文物的故事:文革中,听说有人要砸掉珍贵的石碑和雕刻,百姓马上用石灰或者黄泥将文物覆盖起来,上面大书伟人语录,使文物逃过史上最大浩劫。大仁大义、大忠大孝、大恩大爱,大都是在普通百姓中演绎展现、发扬光大。灿烂的中国文化就在这里延续。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不仅仅是因为它伟大、它重要、它智慧,还因为它作为遗传基因,生长在亿万百姓的细胞里,流淌在血液中。中华文明之河没有断流,是因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是“一而二、二而一”的关系。
百姓充当着载体,传承着文化,这只是事情的一面。事情的另一面,说来就不免令人气短。“最不缺文化”的中国大地,眼下丛生的乱象,却在在表明这里“真没有”文化:信任普遍危机,值得信赖的对象委实不多;伪劣产品成堆;毒食品迭出;官员腐败成风。现象不胜枚举,根子只有一个:人没有被“文”“化”过,不知“尊严”为何物。有尊严的人,既尊重自己,也尊重他人,道德感极强。没有尊严的人,从衣食无着忽然变得有钱或者有权,那“吃相”肯定不会好看,他不知道德廉耻为何物。中国贫弱的日子过于漫长,文化和百姓互相得不到滋润,二者都日渐羸弱。近数十年情况稍有好转,但距离有余暇、有精力去谈文化,尚须时日。如果底层人都不识字、不懂得科学知识,更不会发手机短信和使用电脑,不会在网上买火车票,这“文化载体”也就当得越来越吃力,总有断条的一天,更不要说对文化的宏扬和创新了。民间文化乏善可陈,传承和发展少有亮点,说到底,还是“仓廪”未实、“衣食”未足之故。农民工流血流汗干了一年,不少人却连工钱都讨不到手,他能有心情跟你切磋文化?
近些年底层文化荒凉,缘于忽略日久。这有点像体育(体育也是文化)。各级体育官员,眼珠子盯的是运动会、是赛场。这里经费足,活得滋润;响动大,活得体面;奖牌多,容易升官。群众体育就惨了,经费、场地、设备要啥没啥,政绩更谈不上,官员哪有奔头?后备力量难以形成,就没有什么“可持续发展”可言。连运动员、球员都选不出来,还侈谈什么国民体育素质、经济生产力和国防战斗力?宣传、文化官员也是一样,喜欢抓大戏、抓大汇演、抓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”,至少也搞一下“书画下乡”,比较热闹、好看,而图书馆、文化站、读书角的建设,科技知识的普及,就比较寂寥,难出成果。带个摄像记者下来,拍个好镜头都难。上世纪80年代,我在山西听到一个文化站站长的故事。某县在一个贫困但文化工作搞得很有成绩的地方召开现场会。文化站长把文化站打扫干净,又打了糨糊,用报纸把窗户糊好。
正当他兴致勃勃地把大队人马领来参观的时候,傻眼了:文化站的窗户纸连同糨糊被饥饿的毛驴吃得一干二净。面对着空洞洞的窗户,站长大放悲声,谁也劝不住。这故事让我也心酸良久。我还记得一个东北的文化站辅导老师的故事。东北的冬天冷,活动场地不好找。这位女老师就把学员领到自己家里,在炕上练习民族舞,结果把炕踩塌了,晚上没有地方睡觉。什么是默默奋斗的民族脊梁?这就是。我们的政策必须让这些基层的文化工作者有用武之地,有较好的待遇,绝不能让他们吃亏。这些“微循环”系统搞活了,整个文化的肢体就健壮了。近年来,我对民间兴起的一些“图书馆”组织发生了兴趣。现在这种读书社虽然规模都不大,但已经遍布全国。有的叫“读来读去”读书社,有的叫“一分钱”读书社,还有的叫“一毛钱读万卷书”读书社。有些是微利运营;还有的是半慈善式的运作。我赞佩这些默默无闻的文化建设者,我主张让这些底层文化的中坚力量健康地生存、发展,在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下,让这些运营者不吃亏、不受气,逐渐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实力,这样,普通百姓就增加了提高文化水平的机会。
全体国人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了,比出几个大师、出几台好戏意义更大。现在好作品不多,杰出人才罕见,又何尝不是忽视底层文化、导致土壤过于贫瘠的结果!前天,我读到一条消息,十分兴奋。这消息的题目是《百名农民工明年“公费”上大学》。事情不算很大,但对农民会有极大的鼓舞,这使社会底层向上流动之路有了光亮。北京市总工会这个事办得漂亮。
“为了谁、依靠谁”的说法,反映的是引领者、组织者的角度。从根本上说,文化建设的主体是百姓,文化建设的成果,最后也应该是体现在百姓身上(都成为高素质的公民),而不是官员向上汇报的材料中的一串串数字。既然如此,文化建设的很多事情不妨干脆就一竿子插到底,让民众作为主角自己去办,政府从旁协助,这样或许会做到事半功倍。你想想,世上哪有希望自己永远愚昧的百姓?群众缺乏热情,别人瞎张罗也无用;反之,群众急于用文化提升自己、改善自己的处境,那力量,若水之就下,沛然孰能与之?